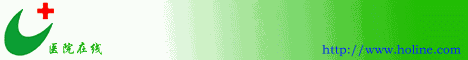|
“性病专家”全家染上艾滋病
“1995年5月3日,我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天:一名本来没有性病的女性到我们科室来检查,我们故意说她患了性病。她的丈夫立即怀疑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要同她离婚。她受不了家人和别人的猜疑和鄙视,服毒自杀了。这都是罪过啊,其实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只是福建沿海的一介渔民。”
2000年2月23日在西安南郊一个单元房里,何艳玲有气无力地对记者说道。
深圳“开诊”失利移师东北重来
1989年2月12日,我同本村的渔民杨新民结了婚。
1989年7月,杨新民和我一起去了深圳,在一家旅馆里匆匆开了一个性病诊所。杨新民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竟然骗过了许多病人,他使用的“先锋”针剂治好了一些病症不太严重的病人,诊所的生意意想不到地好了起来。
不久有关部门开始清查治疗性病的江湖医生,出其不意地“光顾”了我们的诊所,我们被罚了很多钱。迫于无奈,我们只好移师东北一个城市继续从事捞取黑心钱的勾当。
“挂靠”正规医院寻找可靠保护
在东北,我们花钱弄到虚假的证明材料和学历证书,不惜重金收买一些贪财的领导,挂靠在一家正规医院“合理合法”地赚钱。凡有病人来了,杨新民都是摆起“军医”和“专家”的架子,冲人家要很多钱,动不动就要上千元甚至上万元。
1996年,杨新民又重金聘请一些见利忘义的“专家”、“教授”前来坐诊,大肆做广告吹捧这些“专家”的能力如何了得。为了办理广告审批手续,只要有人肯在审批表上盖章或签字,就送人家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好处费。一时间,治疗性病的广告铺天盖地而来,广告费也急剧增高。为了支付这笔巨大的开支,我们便在药费上做手脚,将只值几块钱的药卖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钱。杨新民仍感到利润不够高,又从一些不法商贩手里进一些过期失效药或劣质淘汰药,昧着良心往病人身上用。1997年8月,一位建筑工因为用了我们的药中毒,造成脑神经错乱,四肢瘫痪,成了残废。他的家属来到我们医院论理,杨新民叫来一伙打手将他们打得半死,第二天卷起钱财带着我们一家人逃到了西安。
靠“吓”字宰客用仪器骗财
我们到西安后故技重演,挂靠在一家正规医院的科室,又如以前一样大造声势地为人“治病”。凡是前来就诊者,即使没病也要说成是有病,小病说成大病,大病说成无法可治的重病。病人有疑虑便叫来“专家”吓唬他们,并动员他们的家属也来检查,来一个“宰”一个。不管是否是真正的专家,只要来坐诊,每月便给二三千元的工资,病人不会不信。杨新民还花很多钱买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化仪器放在化验室里迷惑人,令病人深信不疑。其实我们所雇用的化验员根本就不懂化验,他们不管是否有病一律在化验单上划上“+”号。医生根据这些阳性的诊断结论来吓唬病人,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掏出腰包里的钱来。
害人终害己全家赴黄泉
1999年3月,我们又想出另一个绝招,就是给病人开了药之后,并不在病人身上用,而是把它节约下来卖给别的患者。有一个患性病的中年人因为一直挂葡萄糖和生理盐水,没有真正使用消炎药,导致全身溃烂死在我们的诊室里。而另一位女教师则更惨,她压根就没病,只是白带增多,我们却一直说她患了性病,反复为她“治疗”,直到她身无分文的时候才停止治疗。然而,我们怎么也未曾料到,一场灾难降临在我们的头上。那是1999年10月27日,杨新民驾车与一辆大客车相撞,9岁的儿子受了伤,因为失血过多,生命危险。在血库无血的情况下,杨新民为他输血。一些器具都是我们科室提供的,因针头没有严格消毒而形成交叉感染,杨新民感染上了传染病。一个月之后他开始高烧、腹泻、哮喘、头疼、全身出现红色丘疹……时过不久,身强力壮、体健如牛的他在疾病的折磨下,已经变得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了。同时,我的儿子也感染上了同样的病,1999年12月15日,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了。
从此之后,杨新民沉默寡言,情绪低沉。儿子的死使他郁闷不堪。1999年12月31日,他因为病情发作,也痛苦地死去了。
两天之后,我也染上艾滋病——没想到我们替人家“治性病”,自己一家子却染上了艾滋病,这是报应啊!
2月26日,何艳玲也在西安市郊住处死去。
(河南报业网)
评论: 现在,在北京、广东、天津、上海......仍存在着这样的,以挂靠的形式生存下来的“性病专科医院”,靠所谓的专家,当然也可能是那些利欲熏心的“真”专家,招摇撞骗,骗取病人的钱财。说得重些,这些人是在图财害命。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病人自己因为害怕或羞涩等原因,不愿意去正规大医院进行治疗;也有我们正规医院的大夫对这类病人的态度问题,对他们是否太苛刻了?太不够宽容了?要知道,他们同样也是病人,也需要我们的关心和爱护,需要得到同样的治疗;还有,是因为全社会对性病的模糊认识,以及对性病病人的歧视态度,也给了这些“性病专科医院”的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