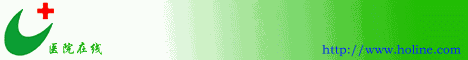2005年临床医学进展回顾 高血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孙宁玲
 孙宁玲 孙宁玲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高血压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留学于西德埃森大学医学院,在心肾高血压中心进修。现任中国高血压联盟副秘书长及常务理事,北京高血压协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学会及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学组委员,北京心血管学会常委。参与并主持国家科委“十五”攻关项目国家星火计划及国家教委211、985的医学攻关课题。参与1999年及2004年《中国高血压指南》的编写,发表文章百余篇。现任《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国循环杂志》、《中华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高血压杂志》及《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等9个杂志的常务编委及编委,并兼任美国JACC杂志、CircuLation、美国AHA系列杂志及《欧洲心脏杂志》等4种外文期刊的中文版编委。现任卫生部心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
高血压涉及许多学科及许多医学领域,近10年来,随着循证临床试验结果的公布,基础领域中多种血管活性肽的发现以及基因工程的进展,高血压的研究已经达到如火如荼的阶段。尽管如此,2005年在高血压专业领域的研究方面仍取得许多新的进展,笔者对一年来发表的主要文献进行了回顾,结合2005年几个重要的国际会议[美国心脏病学会(ACC)年会、美国心脏学会
(AHA)年会、美国高血压学会(ASH)年会、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年会和欧洲高血压学会(ESH)年会]中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以及国际、国内新的高血压指南进行简要综述,供同道们参考。
高血压定义的新认识
高血压以往仅根据血压水平确定诊断。2005年5月,ASH会议提出,高血压是一个由许多病因引起的处于不断进展状态的心血管综合征,可导致心脏和血管的功能和结构改变。新定义将高血压从单纯的血压读数扩大到包括总的心血管危险因素。美国ASH主席Giles指出,“新的定义包括了有无危险因素、疾病早期的标志物和靶器官损伤,更准确地说明了由高血压所引起的心血管系统和其他器官的病理异常”。新定义的高血压分期不仅依靠血压测定,而且还依靠心血管危险的指标,如器官损害来计算。这种概念的更新来源于对心血管疾病危险评估的逐渐实施以及人们对循证医学的广泛理解。
近年来,研究者们越来越认识到高血压是一种与遗传、环境、代谢极为相关的复杂疾病,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当高血压与其他相关危险因素并存时,单纯的血压控制仅仅只能使不到60%的患者获益,而多重危险因素的综合干预才能获得更大的益处。
对高血压诊断方法的进一步认识
人们及医务工作者长期以来以诊室血压作为判断血压水平的标准,近年,动态血压监测(ABPM)技术的开展弥补了一些诊室血压诊断的不足,但人们对此仍重视不够。单纯的诊室血压测量不能识别出那些“隐性”高血压患者[诊室血压正常(BP<140/90
mmHg),而动态血压显示白天血压增高(BP>135/85 mmHg)]及“白大衣”高血压患者[诊室血压增高,(BP≥140/90
mmHg)而动态血压正常(白天BP<135/85 mmHg)]。
2005年,ESH会议及美国JACC杂志公布了一项题为《24小时ABPM评价“隐性”高血压和“白大衣”高血压患者的预后》的报告,在此报告中,研究者对通过ABPM与诊室血压诊断的“隐性”高血压患者、“白大衣”高血压患者及临床明确诊断收缩期高血压(诊室血压BP>140/90
mmHg,24小时动态血压BP>130/85 mmHg)的患者连续追踪随访了10年发现,发生心血管死亡及卒中复合终点的危险,在“隐性”高血压患者为2.13,
“白大衣”高血压患者为1.28,在明确的收缩期高血压患者为2.26。
该研究提示,高血压的诊断应当将诊室血压与动态血压结合,这样才不至于遗漏一些高危的高血压患者的诊断。研究者指出,医生们至少要意识到“常规诊室血压测量可能有漏诊‘隐性’高血压的可能,这一点很重要。在诊室血压及其他危险因素控制良好,但临床却出现靶器官损害及心血管病的时候,要考虑此患者是否存在‘隐性’高血压,至少应当进行ABPM加以判断”。
同期在JACC杂志中的一篇述评指出,“应记住,‘白大衣’高血压的预后属良性,常常因诊室血压增高而治疗过度,对此类高血压治疗宜保守。而‘隐性’高血压的预后要严重得多,但常常由于诊室血压‘正常’而治疗不足。因此全面对血压进行评估,才能更有效地控制疾病。”
梅奥医院Sheps教授认为下列几种情况应当采用ABPM:①ABPM是肯定孤立性临床高血压(白大衣高血压)诊断的最佳方法;②经选择的难治性高血压,在诊室出现收缩期高血压的老年人及妊娠妇女;③评估低血压状态,发作性高血压、体位性低血压及疑似自主神经功能不良的患者;④查体发现有左室肥厚、微量白蛋白尿及脑卒中,但诊室血压相对正常的患者。目前国际更主张将动态血压、家测血压配合诊室血压进行综合分析,一些药物治疗的对比研究(COSIMA)则采用诊室血压与家测血压结合,综合评价药物与药物之间降压效果的差异。
高血压研究领域2个主要亚组临床试验结果公布
1. ALLHAT亚组试验
ALLHAT试验公布于1997年,2005年6月,第15届ESH年会报告亚组结果,亚组集中分析了高血压伴冠心病的患者及高血压伴代谢综合征的患者的终点结果。研究者对高血压伴冠心病患者进行6年降压治疗后发现,不论基线是否存在冠心病,采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赖诺普利与钙通道阻滞剂(CCB)氨氯地平治疗,在致死及非致死性冠心病的发生终点上,2种药物长期治疗无显著差异。在脑卒中终点的发生上,CCB优于ACEI,基线有冠心病的高血压患者,CCB使卒中危险降低29%(P=0.04);基线无冠心病者,CCB使卒中危险降低20%(P=0.03)。高血压伴代谢综合征患者分别接受利尿剂(氯噻酮)、ACEI及CCB治疗6年,3组累积冠心病事件发生率无差异。
ALLHAT亚组结果表明,有代谢综合征的高血压患者接受CCB、ACEI及利尿剂长期治疗,对终点的影响是一致的。在对有冠心病的高血压患者的长期治疗中,CCB与ACEI对降低致死及非致死性冠心病发生终点是一致的,但在减少脑卒中终点的发生方面,CCB优于ACEI。
2. VALUE亚组试验
VALUE试验的亚组单药治疗分析结果在ESH的第15届年会上予以公布。单药分析亚组研究观察了VALUE主研究中15313例患者中的7080例(46%),其中6个月药物调节期结束时仍坚持服用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缬沙坦单药者3263例,服单药CCB氨氯地平者3817例,单药随访时间为3.6年。结果显示,在治疗的全程中,通过诊室血压测量,2个药物组患者的血压降低幅度和心血管复合主要终点无差异,缬沙坦组新发糖尿病及心衰的发生率明显降低。VALUE的动态血压亚组分析显示,氨氯地平在夜间后几个小时的血压降低幅度优于缬沙坦。
新的高血压临床试验公布提供高血压治疗的新方向——优化联合治疗方案
高血压患者治疗达标是关键,然而一种降压药物仅仅只能使30%~60%的患者血压达标,增加药物的剂量虽然可以提高降压疗效,但却可能出现更多的不良反应(增加一倍剂量后,CCB会引起更多的水肿,ACEI会导致更多的咳嗽,利尿剂会导致更多的低血钾),这样反而使患者的依从性降低。因此,联合治疗是高血压的治疗趋势。2005年公布的2项临床试验正是体现了这一趋势。
1. FEVER研究
这是一项中国的高血压临床试验,结果公布于第15届ESH年会,并发表在2005年的《高血压杂志》上。这是一项双盲、安慰剂对照的随机研究,入选了近1万例中国的高危高血压患者,在试验开始阶段,所有患者先接受低剂量氢氯噻嗪12.5
mg治疗,在没有达标的时候随机分为2组,一组接受氢氯噻嗪+非洛地平治疗,另一组继续接受氢氯噻嗪单药持续治疗(可以加量)。持续治疗60个月,主要终点是致死及非致死性脑卒中发生。
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与单药治疗组相比,全程血压进一步降低4/2
mmHg。联合治疗组主要终点致死及非致死性脑卒中降低28%;在次要终点方面,联合治疗组较单药组使心血管事件发生率降低28%,总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降低28%,总的心脏事件发生率降低34%,全因死亡率降低30%,心血管病死亡率降低32%,心衰的发生率降低24%,癌症发生率降低40%。此研究进一步证实,联合治疗优于单药治疗,血压降的低一些更有利于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2. ASCOT-BPLA研究
2005年ESC会议公布了ASCOT-BPLA研究结果。这是目前唯一公布的高血压联合治疗方案之间比较的临床试验。试验共纳入19257例高危的高血压患者(但排除冠心病患者),随机分至CCB(氨氯地平)+ACEI(培哚普利)联合治疗组及β受体阻滞剂(阿替洛尔)+利尿剂(苄氟噻嗪)联合治疗组,试验研究终点分为主要终点(致死性冠心病和非致死性心梗)、次要终点及三级心血管终点。此试验进行至3.5年时,美国安全监察委员会发现,使用β受体阻滞剂联合利尿剂组与对照组相比持续处于不良的状态(心血管死亡明显增多),因而提出提前终止此试验。ASCOT-BPLA试验于2005年6月提前结束。
ASCOT-BPLA研究主要结果显示,CCB+ACEI联合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全程血压进一步降低2.7/1.9
mmHg,主要终点非致死性心梗及致死性冠心病危险降低10%。在相关的次要终点中,全部冠脉事件发生率降低13%,致死及非致死性卒中发生率降低23%,总的心血管事件及血运重建率降低23%,全因死亡率降低11%,心血管病死亡率降低24%。而事先设立的三级终点中,新发糖尿病发生率降低30%,新发肾功能损害发生率降低15%,外周血管病发生率减少35%,不稳定型心绞痛发生率降低32%。在预先设计的15个终点中有10个终点达到显著性差异。
ASCOT-BPLA研究首次证明了一种优化的组合方案在长期高血压治疗中的益处。
CCB 联合ACEI
治疗在降压机制上体现了血流动力学上的互补——既从压力负荷改善血压,又从容量负荷的角度协同使血压下降;从抗动脉硬化的角度来看,2种药物相互协同,还可以协同共同改善代谢的异常。一种优化的联合治疗方案不仅可以更好地降低血压而且有利于血压达标,并对器官的保护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为临床高血压的治疗提供了优化联合治疗的组合方案,从而为高血压合理的联合治疗提供了新证据。
RAS系统抑制剂是否有降压以外的益处
2005年5月,在ASH年会上,专家们对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S)抑制剂是否有降压以外的降低心血管危险的效应问题进行了讨论。
Lowa大学Hunsicker
认为,心血管终点表现出的RAS抑制剂的益处主要源于血压的降低。他指出,在高血压治疗中,RAS抑制剂在保护患糖尿病的高血压患者的肾脏方面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而其他方面(心脑血管)的获益主要是与血压降低有关,他列举了HOPE和PEACE研究。在HOPE研究中,血压降低极微弱但却获得明显的益处,似乎应归于ACEI雷米普利降压以外的好处,但HOPE近期的亚组研究显示,通过24小时血压测量,雷米普利使夜间血压明显降低,这种降低可能显示更大的益处,而不一定是ACEI降压以外的获益。从PEACE研究中发现,在2组血压控制良好一致的情况下,在主要终点上并没有显示ACEI有更多的益处。
同样按照VALUE检验假说,血压降至同等水平在减少心血管事件方面,ARB应优于CCB。然而事实上,不论是VALUE研究的全组还是VALUE研究的单药治疗亚组均未显示两者的主要终点有差异,仅在治疗3~4年时观察到反映对心衰下降有利的证据。在对以往的ALLHAT及BPLTTC研究的荟萃分析中,降压药物ACEI在与其他药物的对比中均未见到有重大事件的差异。对此,Honsicker指出,上述结果说明,降低血压无疑是关键的。
Weir教授提出,降压固然重要,但不能忽视RAS抑制剂对于RAS阻断后的重要作用。HOPE研究的亚组显示,ACEI雷米普利正性影响了许多替代终点,如脑卒中、左室肥厚和新发糖尿病。在ALLHAT研究中,ACEI与CCB相比,使新发糖尿病的发生率降低18%,
而VALUE研究中ARB缬沙坦降低血压的作用稍弱于CCB氨氯地平,但两种治疗的主要终点相似。Weir强调,大多数高血压患者是需要两种药物才能达到所需要的血压水平,而其中一种药物应为RAS抑制剂。
上述讨论比较公正地说明,RAS抑制剂在高血压治疗中具有重要地位,此类药物在某些特定的疾病(糖尿病、肾病)是需要选择的,而对心脏的保护应当在充分的降压基础上实现。高血压患者的降压需要长期持续,ARB有较好的耐受性有利于长期应用。高危的高血压患者常常需要2种以上的降压药物联合应用,而RAS抑制剂是一种较好的联合药物。
高血压研究展望
美国国立心肺血液研究所(NHLBI)是美国权威的,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机构,在它的工作组总结报告中,专家们指出了高血压今后的研究方向。
(一)高血压研究领域存在的主要挑战
1.
近10年,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以新的视角看待高血压,对了解高血压发病机制做出了很大贡献。遗传学的研究方法能够明确某些具体的基因和形成高血压等特征的生物学通道之间的真正因果关系。随着人、小鼠和大鼠基因组测序的完成,识别出的基因和处于中间表型的基因日渐增多,从而使人们更为明确地认识到,只有多学科研究才能对了解高血压的病因取得进一步进展。
2.
科研领域急需在研究设计时不同学科人才的组合。它要求整合基因组、蛋白质组、生物信息学、统计遗传学、细胞学、生理学、数学及计算机化生物学的专门人才同步上马。汇聚这些不同学科的专家共同来开展实验动物模型和人群的大规模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研究。
3.
高血压研究的另一重要难题是减轻由于血压控制不良所造成的脑、肾、外周血管及心脏等靶器官损伤。这些靶器官损伤到什么程度会导致血压的增高?高血压造成这些器官的损伤程度有多大?这些问题是不易探明的。而目前的关键任务是要区分病因和效应这两大难题。
(二)高血压研究应在多学科多领域中进行
工作组提出,如果将高脂血症、动脉硬化、糖尿病、代谢综合征这些疾病抛开,单单研究高血压,将会妨碍高血压病因研究的突破。因此,主张多学科、多领域协作。
1. 继续进行高血压基因型特征的研究
将基因的功能和疾病的易患性与基因组挂钩来研究仅仅是开始。不得不承认某些基因多态性形成了不同的生物通道,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高血压。今后应继续致力于识别出这些多态性:
①今后应当更为广泛地研究高血压患者及动物模型的基因型,在此基础上进行分层研究,以减少遗传和环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② 应强化对影响降压药物反应的功能基因多态性的识别研究。
③应完善与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大鼠模型系的基因敲除方法,使大鼠的基因调整功能与小鼠相同。
工作组专家们认为,对于高血压基因学的研究应当将定量的生物学与数学模型进行较好的组合,这种定量的知识和数学模型组合,将影响血压调节的数百种基因的效应合而为一,对了解相互的作用至关重要。
2. 进一步明确形成高血压的已知因子的生物学机制
高血压是复杂、多基因、多因子共同参与的结果,同时高血压的病理生理又是个缓慢进展的过程。大量资料证明,中枢神经系统在影响及触发心血管事件中具有重要作用。医学影像的进展使得人们能无创地观察到高血压患者的脑、肾及心脏,并能阐明几个关键器官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相互关系及功能不良。近10年来,人们关注更多的是肾脏和中枢神经系统的相互关系在血压稳态中的作用,目前已经有了许多研究中枢和外周神经的手段,因此,今后应当加强神经系统在原发性高血压中作用的研究。
3. 今后将更好地识别出高血压前期的各种表型及生物标志物
对高血压患者,假如能够早期识别出易患事件的风险,并进行预防,那么伴随高血压的病理事件可望推迟。高血压前期是发生高血压和靶器官损伤的一种生物学危险,对这一人群通过什么标志物将他们检测出来尚属难题,可能需要基因、生化、生理等多种方法共同参与完成。
4. 要重视对高血压总的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控制
目前研究的重点是引起危险因素聚集高血压的生物学机制,今后要解决与高血压同时存在的几种疾病(灶性肾小球硬化、肾小管间质病、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病、胰岛素抵抗和脑卒中)的预防与药物治疗问题。
目前认为代谢综合征并不只是一种胰岛素抵抗状态,还是一种促炎状态,脂肪细胞是一种动态的内分泌细胞,它们可产生相应的脂肪因子(肿瘤坏死因子、瘦素和IL-6),这些脂肪因子对血压对胰岛素的作用和血管炎症,以及与RAS诸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细胞因子如何参与高血压的调节还需要继续阐明。
总之,今后的研究领域应针对高血压的主要病因、参与高血压形成的危险因素以及临床治疗中高血压未能控制的行为问题进行研究。高血压的新治疗包括调控转录的药物、基因治疗、线粒体能量通道内诸种酶的新抑制剂以及新的药物和测量技术等。在高血压的临床治疗领域将会继续按照指南的方案实施,循证医学的证据仍是临床高血压治疗参考的依据,但循证医学的局限性也会为个体高血压的治疗带来偏差。因此,综合整体心血管危险因素,积极强化血压的达标治疗,在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上仍是主导任务。
|